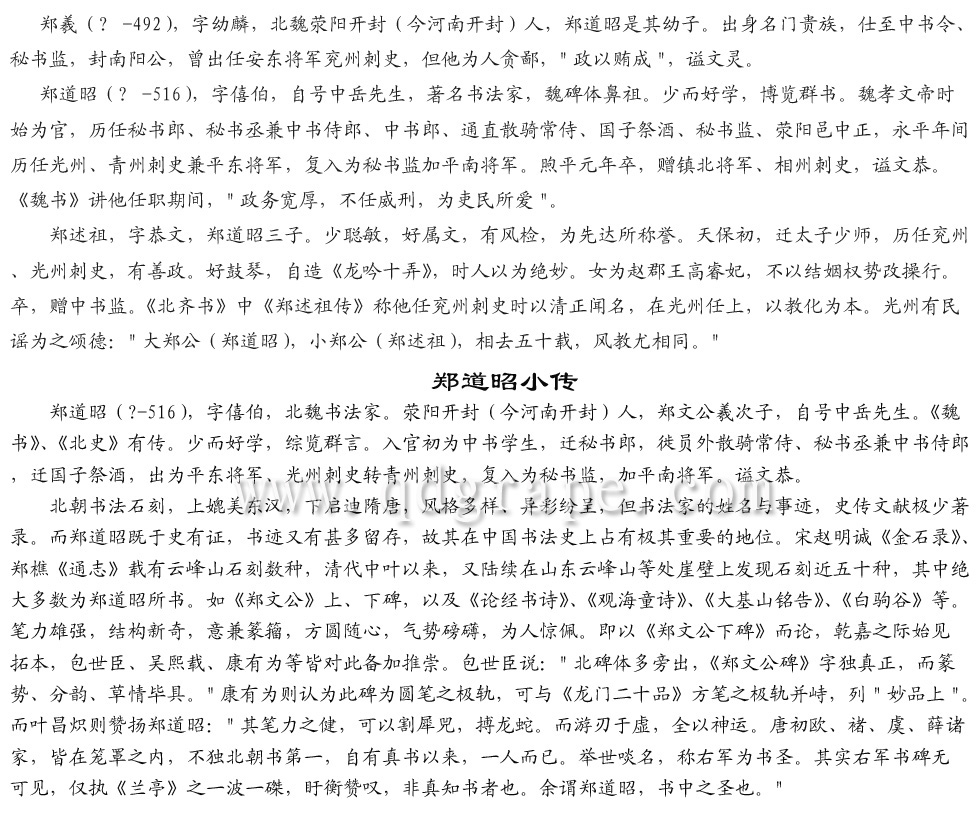 |
| 附:关于郑文公碑的作者 |
| 崔传富 |
 |
有可无。山东大学孙坚奋先生认为荥阳郑氏以经济起家,以文章名世,故道昭父子之善书不见于传记,似为政名所掩,也同样有牵强之嫌:崔浩为汉族大姓之首领,其政名比郑道昭要显赫得多,但同样享有书名并见于传记,书名与政名同垂青史的代不乏人,枚不胜举,何独与郑道昭无缘?
纵观历史上的艺术家,大都在世时,其艺术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当然也有少数艺术家在世无闻,死后名显。这类艺术家无怪乎两种情况:一种是艺术实践超前,超过了时人的接受能力;一种是生前穷困潦倒,但性格孤傲,无力也不愿张扬自己。显然,郑道昭不属于这个范围。唯一的解释是,郑道昭好为诗赋,长于吏治,但不擅书。
刘海粟先生说:"以郑道昭所处的时代、出身、教养来说,写出这么好的字来是完全可能的,但书香门第,甚至有书法气氛的环境中长大而不工书者亦有之。即以郑羲长子景伯来说,史书言其"涉历经史",也未说他工书。道昭数子,述祖而外,皆无工文善书之名"。郑道昭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而真正留下两通碑刻的艺术家恐怕永远湮没无闻了。
二、碑刻中亦未提及郑道昭工书
查云峰四山刻石中,均未言及郑道昭善书,只在《郑文公下碑》中,有道昭"才冠秘颖,研图注篆"的句子,好像与书法沾上一点边,为后人认为郑道昭工书提供了佐证。其实"研图注篆"是指郑道昭作过典籍、文书之类的工作,与上碑"研图注史"涵义一致,是说郑道昭深明"八索九丘、河图洛书"之旨,通达经史古籍,不能望文生义解释为善于篆书,或穿凿为善于书法。碑文称郑道昭"才冠秘颖",颇有张扬的意思,在书法上自掩其名,也很令人费解。
三、上下碑未署名为郑道昭书
按北朝碑刻造像惯例,大都不署书家姓名,但也有例外。如肖显庆书《孙秋生造像》、王远书《石门铭》、朱义璋书《始平公造像》。上、下碑未题书家姓名,也实属正常,但正因为未署姓名,也就不能武断地认为是郑道昭书丹。
郑道昭晚岁"爱仙乐道",流连山水,但郑氏身为中原望族,其骨子里崇尚儒教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时刻不会忘记立德、立言、立身以使家族"绵荣千载,联光百世"。所以,云峰山《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天柱山《东堪石室铭》等诗刻,其诗均注明为"郑道昭作",也就很符合郑道昭的思想轨迹。北朝对书法的重视程度虽不如隋唐以后,但善于书法对一个文人士大夫来说也是荣耀之事,诗刻中题署诗家姓名,却隐去书丹人姓名,失去如此好的扬名机会,也不符合郑道昭的思想愿望。
云峰诸山其他刻石上也大都未题为郑道昭书,仅"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之手书"题刻中有"郑公之手书"字样。郑道昭自称郑公,有悖常理。认真审视此刻,"郑公之手书"5字与前题"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当属随从道昭出游的佐吏所为。据此判断,前题似为郑道昭书。我从来不否认云峰四山上有郑道昭的笔迹,事实上,让一个饱读诗书,好为诗赋,喜欢流连于山川胜迹的文人不留下鸿爪遗痕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据此断定云峰诸山刻石均为郑道昭父子所书,尤其不能断定上、下碑为郑道昭手书,因为该题刻与上、下碑之字无论从用笔、结体还是从风格上看,均非出自一人之手。
相反,上、下碑中对作者有明确交待:上碑第15行、下碑第40行均有"於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烋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的记述。据《魏书·郑羲传》记载,郑羲死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3年),次年归葬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后,痛感葬地遥远,不能按时祭奠,于是邀请程天赐等门生故吏六十余人为其故主撰写碑文,并"铭之玄石",也就是说碑文作者和书丹人均非郑道昭。我一直迷惑不解:碑文中清楚地交待了作者,后人为什么非得把这道耀眼的光环套在郑道昭头上?
四、郑述祖亦未说《郑文公碑》为道昭书
郑道昭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接替王琼,携家眷赴光州治所,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第二年,在天柱山为其父主持刊造《郑文公上碑》。后因在云峰山觅得佳石,再刊《郑文公下碑》。50余年之后,其子郑述祖出任光州刺史,作《重登云峰山记》,中有"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者,今尽零落唯吾一人重得来耳"之句。说明昔年郑道昭在光州任所时,郑述祖是了然于胸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郑述祖在天柱山和云峰山留下的刻石中,却未明言上、下碑是其父所书。
山东平度的于书亭先生,是研究云峰诸山刻石的专家,有若干论文行世。于先生认为上、下碑是郑道昭手书,其主要证据是引用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四言诗残刻》、《天柱山铭》等刻石中的语言,以证明郑道昭是《郑文公碑》的作者。我尊重于先生的学问和人品,但对于先生的这一观点却不敢苟同。
1、《重登云峰山记》中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言泪下"之句。于先生认为"若不是父书,临碑省字,断不能泪下"。于先生在这里对文人笔下带有感情色彩的描写太过于认真和计较。郑述祖"自幼游此",五十二年之后旧地重游,见到了父亲主持刊造的祖父的碑刻,时父亲已故去数十载,江山依旧,生死茫茫,睹物思人,自然会生出无限感慨,何必非要见到"父书"才会"发声哽塞","兴言泪下"?
2、《重登云峰山记》中还有如下文字:"此山正南三十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号……其山上之阳,先有碑碣,东堪石室,亦有铭焉"。于先生认为:"按其文义,'先有碑碣','亦有铭焉',是否指先君所为,亦值得研究"。我认为此文看不出有郑道昭书写上碑之意,而是很清楚地说明天柱山之阳有先祖的碑碣,东堪石室内有父亲的诗刻《东堪石室铭》。
3、上碑碑趺左侧有《四言诗残刻》,最后两句为"泣观遗碣,号诵余篇",于先生断言:"若非祖碑、父书、己诗,断无此情感"。我以为"泣观遗碣,号诵余篇"所抒发的感情与《重登云峰山记》中"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言泪下"如出一辙,只能说明碑是父亲所立,是先君遗物罢了,不能肯定即为父书。
4、《天柱山铭》:"于此东峰之阳,仰述皇祖魏故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文贞公(指郑羲)迹状,镌碑一首"。于先生认为"从'仰述皇祖……遗状,镌碑一首'来看,似寓郑道昭所为"。从字义上来看,确实是郑道昭所为,事实上,《郑文公碑》也是郑道昭一手操纵搞起来的,郑道昭为"皇祖""镌碑一首",亦即我们今天所言"某某人为先辈刻碑一块",碑是谁刻的?当然是匠人;碑文是谁起草的?当然是请有名望之人捉刀;碑是谁书写的?毫无疑问是请书坛高手为之。并不是说某某人为先祖立碑,就一定是某某人为先祖写碑,他只是主持并出资筹办罢了。
五、"麐"、"驎"之误,有悖常情
上碑中郑羲的字为"幼麐",而在下碑中却莫名其妙地变为"幼驎"。"麐"与"驎"是异体字,虽音义一致,但写法迥异。古人名字用字是相当讲究的,尤其是文人学士,取字和取号,慎重而严谨,不可能随意更改。《魏书》中郑羲字"幼驎",《北史》为"幼麟"是属于后人写史,两书作者并非一人,成书时间跨度也很大,偶有误记,无可厚非。但上、下碑刊刻于同一年,且出自一人之手,他人撰文作书出此错误已属不该,若为郑道昭书丹,写错了父执的名字,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了。
六、子为父书碑,有违世俗
子为父撰写碑文,在汉魏六朝个人文集中极少见到,况且上、下碑文中没有使用第一人称,而是使用了第三人称,是他人的口吻,因此碑文显然不是郑道昭所为。
南北朝时,至今还没有见到子为父书丹碑文的例子。一个出身豪门大族,身为从二品高官的郑羲死后竟无人为之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还得由儿子亲自为其颂功扬名,既不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和名望,也有悖世俗。这种遭人讥议的事情,决非郑道昭所为。
《郑文公碑》的作者应该是程天赐等新旧僚佐,在上、下碑中均已提及,且符合东汉以来以至于南北朝时期故吏为其府主撰写碑文的习俗,应当是可信的。
七、未避名讳,有悖常规
南北朝时期,避家讳之风甚盛,闻讳必避,动辄得咎。以至于闹出"闻讳必哭"的笑话。颜子推《颜氏家训》中载,臧严之子臧逢世"往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竟修笺书,朝夕辐辏,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记取,多废公事"。而象郑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如儿子为父亲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直书父名而一点不避家讳,确有悖常理。郑述祖《天柱山铭》中多处颂扬其父公德及政绩,但无一处直呼其名,均以"公"字代之,且在"公"字之上空出一格以示尊崇。郑道昭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又常年担任"秘书郎"、"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中书侍郎"、"国子祭酒"、"司州大中正"等京城低、高职文官,熟知朝典,广有美誉,怎会在闻讳必避的世风笼罩之下为其父书碑而毫无顾忌呢?
八、篡改谥号,怎敢书丹
郑羲卒,尚书奏谥曰"宣",诏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改谥"文灵"。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灵"乃无道之谥也。郑羲卒于兖州任上,次年葬于河南荥阳,一直未曾立碑。其后十九年,郑道昭在光州所辖之天柱、云峰二山先后刻石立碑,以为先君歌功颂德。为避其父恶谥,碑中称郑羲为"文公",而避口不提"灵"字。其时北魏政权已从孝文帝换成了宣武帝,光州任所离京城洛阳远隔千里,颇有山高皇帝远的味道。但郑道昭久为京官,熟知本朝典章制度。作为朝廷命官,冒欺君之罪,擅改皇帝亲自钦定的谥号,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为避祸患计,郑道昭不能亲自为文书丹,而只好请郑羲故吏或官衙僚佐为之,他只是幕后操纵罢了。这样既不授人之把柄,又达到了纪念先君,歌功颂德的目的,也符合上层社会汉族高官的心理,可谓煞费苦心。
九、年高位显,无力书丹
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郑道昭卒于洛阳晖文里,时年约61岁。其主持刊造《郑文公碑》时,已经56岁,在今天看来正值壮岁,但在当时已是年届花甲的垂暮之人了。凡到过天柱山的人都知道,天柱山孤峰拔地而起,山势陡峭,国家投资兴建碑亭和整修山路后,沿石阶而上,犹觉路仄险峻,令人头晕目眩,可想当时登山之难,而立于山阳的上碑巨石,连同碑趺3米多高,突兀前倾,下临无地,连搭支架尚有困难,一个年近花甲之人,要在此斑驳巨石上写上881个4、5厘米见方的楷书字,其难度之大,非体力所能及。而同年刊于云峰山的下碑,计1244字,字径5厘米,也是一篇洋洋巨制。不算云峰、天柱、大基石山上的其他刻石,仅这上、下二碑,2000余字的碑文,而且要做到字字严谨,笔笔精到,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对统领三郡、十四县,十六余万人口的胶东地方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郑道昭来说,他那里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呢?
我曾陪武汉徐本一先生登临天柱山。徐先生观看了上碑险要的地势和布置谨严、书写整饬的碑文后,认为不可能是书丹后刻石,直接书丹,难度太大,无人能及,一定是先书于纸上,再移于石上的。但上碑是一块天然碑状石,碑面凸凸凹凹,斑驳不平,我认为以当时的技术,从纸上移于石上是有困难的,几乎没有这个可能。从此碑的质地上分析,只能是书丹上石;从山体和碑石的险要程度分析,只能由年轻体壮的书家为之。当时,郑羲的故吏程天赐等人19余年之后均垂垂老矣,为文尚可,亲自书丹已无可能。书丹者应是随侍郑道昭左右,年轻有为、书艺超群的僚佐或亲朋。
十、结语
郑道昭以宣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来到光州刺史任上,首次出任地方官。当时,其父葬于荥阳已十九年,恶谥在身,一直未能树碑立传,葬地与任所遥隔千里,不能按时祭奠,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官场的失意,使他谈经访道,流连山水,光州的壮美山川使他萌发了为先父树碑立传的念头,而且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也可以删去"灵"字恶谥。于是程天赐等郑羲门生故吏60余人在郑道昭盛邀之下来到光州。旧地重游,感叹唏嘘之后,用饱含感情之笔,为自己的老上级写下了充满溢美之词的碑文。道昭即令人在天柱山上事先觅好的一块高大的天然碑状石旁搭好支架,将碑面稍加琢磨,请身边一名精于书艺又年轻力壮的僚佐或友朋书丹上石,复请工匠雕刻下来。稍后,又在云峰山之阴觅得佳石,便略增其文,又刊一碑,故名下碑。--两处令后人顶礼膜拜的碑刻诞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这里否定郑道昭为《郑文公上、下碑》的作者,丝毫没有贬低上、下碑书法艺术的意思。《郑文公碑》是历史瑰宝,将永远光照史册;也丝毫无损郑道昭在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他在任光州、青州刺史期间,主持刊刻了如此众多而又集中的艺术精品,是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的名字将随着云峰诸山刻石书法艺术存在而永远流传下去。
|
|
